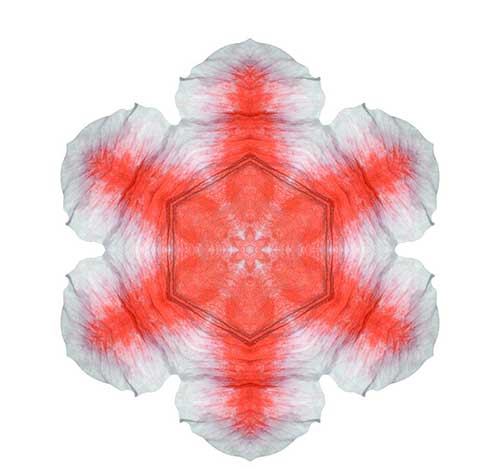佛教在西域传播之时,又由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当时由贵霜王国通往西域到敦煌有两条路线(亦称官道)棗一条是:越过葱岭,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行进,经过莎车、于阗(今和田)、尼雅(民丰)、且末、鄯善(若羌)和楼兰,然后过玉门关到敦煌;另一条是:越过葱岭,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关进,经过疏勒(今喀什)、姑墨(阿克苏)、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和伊吾(哈密),然后到达敦煌。还有一条小道,由克什米尔入红其拉甫山口,经子合、皮山到于阗。这3条路线均勾通了塔里木与中亚和印度的联系,把东方与西方连结起来。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贵霜王国的佛教艺术也进入了西域地区,在塔克拉玛干南北两条路线上都发现过早期佛教艺术遗存。其中,发现的迄今为止最早的遗迹是1959年在民丰县发掘的一座公元2世纪的墓葬,出土的一件棉织布上,印有腊染的供养菩萨和残缺的佛像;另外,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固若羌发掘了一座不晚于3世纪的佛寺遗存,其寺礼拜道外壁面的壁画一派中亚风格,内容主要表现了释迦说法和佛传及本生。可见,当时佛教在西域已相当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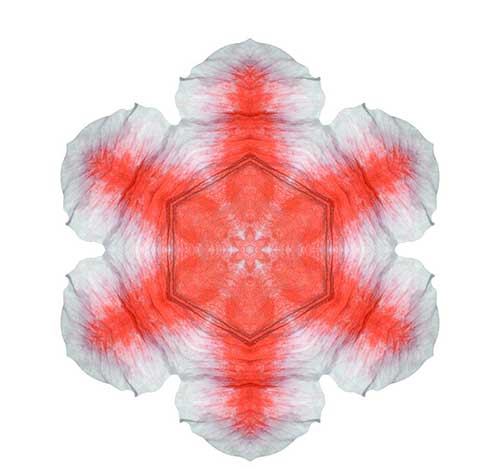
据史料记载,佛教传入中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西汉末年,公元前2年(哀帝元寿元年)有“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录;东汉初年,明帝(公元58~75年)夜梦神人,以为佛,遣使西行,在西域抄回佛经42章,于洛阳城西雍门首建佛寺(白马寺),并有楚王刘英(明帝的异母弟)晚年喜黄老、学浮屠、斋戒祭祀,奉献黄缣白纨,“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棗男居士)、桑门(沙门)之盛馔”等事。可见佛教在西汉末已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东汉初已有初步的流行,并且有少数居士、沙门存在了。 公元70年,楚王刘英以结交方士、造作图谶,被控告以密谋造反罪。这时候的佛教徒一般被人们视做方士一类,佛经也被当成谶纬来看待,这不仅反映了西域佛教的重要表征,也说明朝野人士对巫术化的佛教的一种认识。佛教之所以能站住脚,与两汉之际被称为道术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受到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有很大关系,据《后汉书》记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用符命,及光武尤倍谶言,士之赴趋时宣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也。”在这种背景下,虽然某些僧协和反对“诵咒行术”、“半自然火”等异道行为,但仍不能制止这种趋向的发展。早期来华的知名僧侣,如安世高、支娄迦谶、佛图澄、昙无谶等,都同时以巫术见长。应该说,佛教的巫术化是佛教向大乖过渡的重要阶段,由此大乖佛教向多神主义发展。 佛教初来汉地,开始只是在上层社会的王室皇族、贵族地主中有些影响。在大城市中,不多的佛寺只是供西域来华的僧侣和商人们使用,在法律上不允许汉人出家为僧。至终汉之世,佛教尚未形成了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未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至于三国,研究般若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对《般若》的讲习在魏、吴两国都有相当的开展。但是,魏自曹操开始,将民间的鬼神祭祀作为“淫祀”加以禁止,并严格限制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故魏境的佛教重视对戒律的译介,反映出相当数量出家的僧侣对内部纪委整顿和规范的需要,这都是与曹魏对宗教禁约有关系的。与之相对,孙权的东吴集团对佛教却采取了宽容与优待的政策,使佛教在江南一下子有了较大的发展,与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支持佛教是东吴王室的一个基本态度,并由此作为开端,成为六朝王室对待佛教的基调。 公元280年,三国归晋。公元290年,晋武帝死,西晋皇室宗亲间爆发“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乖隙逐鹿中原,北部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分裂与混乱之中。此时,佛教却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大国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后赵帝羯人石勒(公元274~333年),提倡经学,起用士族,以汉文化教化各族民众;同时推崇神僧佛图澄,与狂乞者麻{礻需}、禅者单道开等,共以神异惑众,大兴佛教。氏族的前秦帝苻坚(公元338~385年),攻破襄阳后,以“贤哲者国之大宝”,俘名僧道安回长安,集“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后秦姚兴(公元366~416年)击败后凉,迎鸠摩罗什入长安,集沙门5000,开十六国中文化最繁荣的朝代。匈奴酋长沮渠蒙逊(公元368~433年),称王北凉,畅通了与西域诸国的往来,他大力兴造佛像,又请来昙无谶译经,促进了佛教的普及,影响远及长安、建业,使姑臧成为西域佛学的重镇。 西晋之后,东晋偏安江南。流行于魏吴西晋的佛教般若学,渗透到上流士大夫阶层,涌现出的名僧和议论佛理的名士越来越多。这时玄学的理论重心,已转向佛教的义学方面。名士奉佛,有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继承玄学中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传统,同《般若》《维摩》的大乖空宗接近;另一种是趋向于佛教有宗,试图调合佛教同儒家的正统观念,注重因果报应和佛性法身等说法。佛教在江南社会迅速扩展的原因,还有赖于帝王贵族浓厚的崇佛之风。东晋诸帝,无一不信奉佛教,结交僧尼,他们予沙门以特殊的礼遇,更有甚者可以出入宫廷,干预政事。考武帝时的尼姑妙音,可谓显赫一时,公卿百官竞相巴结,她在当时“供亲无穷,富倾都邑”,“权倾一朝,威行内外”,从而浮现出一种扭曲的社会现象。士大夫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百数,却并不接济亲友贫困。皇室贵族大兴土木,竞相修建寺庙,成为东晋王朝奉佛的一个特点,据唐法琳《辨正论》载,东晋共有佛寺1768所,僧尼24000人。这说明,一个前所未有的阶层即僧侣阶层在社会中形成了,佛教在汉地站稳了脚跟。 佛教在东晋十六国的普及与发展中,成为争取各民族共同支持的一种信仰,从而增进了南北各族人民的了解与沟通,这在当时分裂的时局下,对于模糊胡汉各族的民族界限,维系一种共同的心理认同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佛教对在一定限度内阻止杀伐和稳定社会起到了作用。石勒、石虎在历史上以暴虐残忍著称,面对这样的暴君,佛图澄力劝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吓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终无福佑”。《僧传》说石勒听了佛图澄的劝谏之后,“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道安(公元312~385年)受东晋之邀至襄阳,一居就是15年,时襄阳为东晋抗胡的前沿阵地,道安久居此地,实有安抚军士,稳定民心的用意。公元378年,苻坚围攻襄阳,道安分散徒众,自己却与守将朱序共守城池,次年2月,城破被俘。苻坚视道安为“神器”,安置他在长安五重寺,予以优渥,道安成为北方学界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道安仍然劝说苻坚不要过江攻晋,虽未成功,却表达了他对汉民族正统的东晋政权的热爱。 魏晋天下多故,士大夫崇尚玄学,鼓吹“以无为本”,“以寡治众”。然而,玄学多务清谈,不涉世务,虽风靡一时,却始终在名士豪族之中转圈子,未能深入和影响到社会下层,所以,到东晋以后,玄学思潮就告终结了。但是,玄学本身的精致思辨与魏晋名士善结佛师和崇尚玄谈之风给佛教般若学的驻足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玄学关心的是名教与自然,佛教关心的是世间与出世间,这两大问题都能够归结到本末、有无这一对总范畴之下。佛教是出世的哲学,但它这时却是以出世的姿态关心着世间,试图协助王化,尽力治道,因此,玄佛两家的“所以迹”是一致的。道安把般若的“空”理解为本体、无,否认现象的真实性,只承认本体的空寂;道安的弟子慧远(公元334~416年)继承师说,以本无为法性,也就是以般若性空为实体。师生二人的观点与王弼的“以无为本”的说法基本一致,被称为“本无宗”。当时对般若学理解和阐发的不同派别,统称为“六家七宗”,“六家七宗”的解释虽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都是对玄学化的《般若经》中的所谓的“空”的意义之不同看法。“六家七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经论的解释权转移到中国知识僧侣手中,佛教在汉地也找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入口与依据,遂成为中国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输入我国中原,先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后与魏晋玄学合流,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并由此走向了南北朝时的独立发展道路和隋唐时的鼎盛时期。

本文链接:佛教传入汉地
上一篇:佛教基本生活礼仪
下一篇:佛教几位常见菩萨的精神内涵